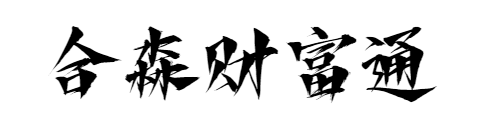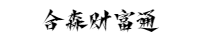茅台能否化解贵州债务?_地方_投资_财政
原标题:茅台能否化解贵州债务?
这并非无稽之谈,历史上贵州省政府曾经两次这么操作:2019年和2020年,茅台集团分别将4%的贵州茅台股份无偿划转至贵州省国资运营公司,实施“茅台化债”方案

文 | 清和
近期,贵州省政府一研究中心在当地调研发现,各地化债工作推进异常艰难,“仅依靠自身能力已无法得到有效解决”。这被解读为当地对债务难题“摊牌”。
贵州省一年公共预算收入不到1900亿元,显性债务规模1.2万亿元,负债率61.8%,排全国第二。不过,有网友提出,贵州茅台可轻松化债。贵州省政府持有茅台集团90%股权,茅台集团持有贵州茅台54%股权,按当前贵州茅台2.2万亿元总市值计算,贵州省政府持有市值大约1.07万亿,基本可以覆盖显性债务。
地方政府为何负债累累?股权财政能否化债?
本文从贵州入手分析地方债务的成因和化解办法,重点分析资源错配、股权财政和财政软约束。
本文逻辑:
一、资源错配:人口向东,投资向西
二、债务经济:土地财政,股权财政
三、财政扩张:软性约束,硬性约束
资源错配:人口向东,投资向西
贵州债务早有预警。
先看一个著名的县级债务案例。独山县,位于贵州南端,经济基础差,2018年财政刚突破10亿元,2020年才摘掉贫困县帽子,政府负债却高达400亿元,年财政收入抵不上利息,被认为最能借钱、最会花钱的贫困县。
从2010 年开始,当地政府激进借债、大兴土木,兴建“天下第一水司楼”耗资2亿元,建设造价20亿元、面积1.5万亩的大学城,还投资56.5亿元的盘古庄、4.5亿元的天洞、13.5亿元的赛马场、15.2亿元的古城、6亿元的万户水寨、10亿元的大数据中心,而这些项目基本因现金流枯竭而烂尾,最终将该县财政推入债务深渊。
再看一个市级城投债案例。遵义道桥,为遵义市最大的完全国有控股的城投平台公司,主要经营基建、市政和房地产业务。根据该公司2022年中期报告,截止到6月末,遵义道桥总债务余额为457.54亿元,其中短期债务余额为141.41亿元,现金短期债务比只有0.04,部分债务已出现逾期;上半年营收6.73亿元,同比下滑36.29%,实现归母净利润-2.86亿元,同比下滑16.74%。
2022年12月30日,遵义道桥宣布银行信贷重组,涉及债务规模155.94亿元,重组后银行贷款期限调整为20年,前10年仅付息不还本,后10年分期还本。需要注意的是,本次债务重组只是银行贷款部分,另外还有300亿元左右城投债、非银行贷款等债务待偿还。
再看贵州省级财政与债务。2022年,贵州省GDP为2.01万亿,人均GDP5.2万元,全国排名均靠后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886亿元,支出5849亿元;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2041亿元,支出2290亿元,全年两本账收支缺口4212亿元。全省政府债务规模1.24万亿元,其中一般债6588亿元,专项债5881亿元。负债率(债务余额/GDP)为61%,为全国第二。
当然,地方债务问题不是贵州独有,若以负债率为标准,我们会发现,经济落后省负债率偏高,主要集中在西南、西北和东北地区,东南沿海的经济大省负债率更低。
在2022年各省负债率排名中,青海第一,负债率84.3%,债务规模3044亿元;之后依次是贵州、吉林、甘肃、天津、海南,负债率均超过50%;接下来是黑龙江、新疆、云南、内蒙古,负债率均超过40%。而江苏、上海、广东、福建负债率最低,均不超过23%。
为什么经济落后省份负债率更高?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资源错配。
过去十多年,“孔雀东南飞”,全国各地人口大规模向东南五省市集中,其中东北人口流失最为严重,而“挖掘机一路向西”,公共投资大举向西南、西北挺进,其中西南地区基建投资尤为火热。
数据显示,从2010年到2022年,广东、江苏、浙江、福建和上海常住人口合计增长4660万人,增长率为15.66%,其中广东常住人口增量就超过2200万人;同期,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东北三省常住人口减少1312万人,增长率为-12%。过去12年,西南地区的常住人口其实所有增加,但是近些年增长缓慢、甚至有所下降。云南常住人口在2020年达到峰值4722万人,2022年下降到4693万人,减少29万人;贵州常住人口同样在2020年达到峰值的3858万人,2022年减少2万人。
最近十多年,西南地区的投资高歌猛进。
从2019年到2018年,西南固定资产投资进入“狂飙”时代,贵州年均增速25%、云南年均增速22%,而同期广东和江苏年均增速为15%。其中,2011年、2012年贵州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高达40%、31%。
图:广东、江苏、云南和贵州固定资产投资,来源:wind 智本社
2019年开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全面下降,其中贵州降幅最大。从2019年到2022年,贵州、云南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均值分别下降至-1%、6.9%,同期广东和江苏年均增速分别为5.5%、3.75%。
钱往哪里投?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有三大类:基建、房地产和制造业。
以贵州为例,从2009年到2013年,房地产投资高速增长,增速大幅领先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。其中,2011年上半年期间,房地产投资累计增速一度接近100%。2014年到2018年,房地产投资增速快速下滑,取而代之的是基建投资,基建投资增速跑赢固定资产投资增速。2019年到2022年,贵州固定资产投资结构艰难调整,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增速迅速掉落到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之下,制造业投资在大震荡中提速。
以高速公路为例,从2008年到2021年,云南高速公路里程增长296%至9947公里,贵州增长767%至8010公里,同期广东增长189%至11042公里、江苏增长35%至5023公里、浙江增长69%至5200公里。贵州、云南高速里程先后超越浙江、江苏,直追广东。
图:广东、江苏、浙江、云南和贵州高速里程,来源:wind 智本社
与东部地区相比,西南地区的基础设施落后,基建投资补短板无可厚非,但是出现投资过度现象。
以人均高速公路里程为指标,贵州每万人高速公路里程为2.08公里,云南2.12公里,而广东只有0.87公里、江苏0.59公里、浙江0.8公里。以每公里高速公路对应的经济产值为指标,贵州每公里高速公路对应的GDP为2.4万元,云南2.7万元,而广东达到11万元、江苏23万元、浙江14万元。
尽管还需要考虑地形条件、社会扶贫等因素,但是这种比较依然可以看出高速投资的经济效率差异。贵州高速总里程、人均里程均超越浙江、江苏、湖南、湖北、山东等经济大省,还超越全球第三大经济体日本,但GDP以及每公里对应的经济产值与后者相去甚远。
人口跟着市场跑,财政按计划分配,空间错配导致资源浪费和债务增加。
当然,这只是表面现象。
债务经济:土地财政,股权财政
经济弱省为何有钱投资?
一方面是转移支付。
数据显示,2022年,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最多的省份是四川,规模6486亿元,人均0.77万元。另外,云南4435亿元,人均0.95万元;贵州3650亿元,人均0.95万元;甘肃3209亿元,人均1.29万元;内蒙古3287亿元,人均1.37万元。而广东、浙江人均转移支付均只有1000多元。
结合转移支付和财政上缴,只有广东、上海、北京、江苏、浙江、山东、天津、福建和辽宁对全国财力保持正净贡献,四川、黑龙江、河南、新疆、甘肃、贵州、云南年净贡献值均低于-1700亿。
贵州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只有1886亿元,而转移支付3650亿元,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两倍,加上转移支付缺口缩小至313亿元。如果没有转移支付,那么贵州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缺口高达3963亿元,为收入的两倍多。如此,贵州自然没有足够的财力大规模投资。
当然,转移支付的资金用途非常广泛,其中不少投入到民生领域。不过,资本是灵活的,转移支付的资金多了,地方财政就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项目投资中。
另一方面是地方债扩张,尤其是城投债快速增加。
城投债崛起于2009年四万亿“救市”。当时,地方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大规模借债,但是政府不能直接向银行贷款,只能发行地方一般债和专项债,后者发行需要财政部和发改委审核。于是,各地纷纷成立国有城投平台,地方政府授权授信城投平台发行城投债融资和向商业银行贷款,进而大规模投资基建、房地产、市政等项目,最终给地方政府带来巨额的土地出让金收入,即土地财政。
经过2009年和2016年两轮地方债务扩张,商业银行、城投平台、基建和房地产投资、土地财政已形成了一股庞大的势能。地方政府高度依赖于由土地金融驱动的土地财政。而与土地财政持续增长相对应的是地方隐性债,主要是城投债。像上面的贵州遵义道桥就属于地方城投平台,其450多亿债务属于地方政府表外的隐性债务。
目前,地方债务风险最大的是以城投债为主体的隐性债务。全国城投债规模预计在40-60万亿之间,近些年集中到期,年均到期量超过3万亿。
经济落后省市的城投债占比更高。原因是,越是经济落后省份,越是到市县级城市,一般债和专项债融资难度大,越依赖于城投债,同时隐性债务更重。
这里使用罗志恒老师的研究数据(2021年),广义债务率最高的是天津,达到530%,其中带息城投债1.2万亿元,超过地方债规模;其次是贵州、云南、四川、重庆,广义债务率均超300%,其中四川带息城投债3万亿元,重庆带息城投债1.7万亿元,均为地方债两倍多;贵州和云南带息城投债均为1.1万亿元,均与地方债规模相当。值得注意的是,江苏、浙江的城投债规模也很大,广义负债率超过300%,而广东城投债规模要小得多、广义负债率为165%。
如何化解地方债务问题?
有人提出“茅台化债”方案:贵州省政府是茅台集团的大股东(持股比例90%),茅台集团持有贵州茅台54%的股权。参考当前贵州茅台市值推算,贵州省政府持有市值达到1.07万亿,基本可以覆盖显性负债。贵州省政府可以通过出售茅台股票或股权质押融资的方式偿债。
实际上,这并非无稽之谈,历史上贵州省政府曾经两次这么操作:2019年和2020年,茅台集团分别将4%的贵州茅台股份无偿划转至贵州省国资运营公司,实施“茅台化债”方案。
“茅台化债”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股权化债的方案。
最近十多年,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持续增加,同时土地、国企、矿产等国有资产也在持续增加。
数据显示,从2017年到2021年,全国国有企业资产增至308.3万亿元、负债增至197.9万亿元,国有资本权益增至86.9万亿元,年均增长14.6%;国有金融企业资产增至352.4万亿元、负债增至313.7万亿元,国有资本权益增至25.3万亿元,年均增长11.8%;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增至54.4万亿元、负债增至11.5万亿元,净资产增至42.9万亿元,年均增长20.3%。另外,全国国有土地总面积52346.7万公顷,其中国有建设用地1796.3万公顷、国有耕地1955.5万公顷。
李迅雷老师提出用股权财政取代土地财政。他对股权财政提出了约束条件:提质增效。通过“管资本”和市场竞争的方式做大国有资产,“让国有资产回报率提高一个百分点,就有3万多亿元的收益增量”。
早在300多年前,威廉·配第就在其著名的《赋税论》阐述了这一方法。威廉·配第在谈到如何才能更好地征税时,提出了另外一种办法: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全部土地中划出大约六分之一的土地,大约四百万英亩,作为国王的领地。国王收取地租,大约为两百万镑,作为税收以支持公共开支。
威廉·配第认为,国有地租等同于纳税,那么民众就可以免税,或减少纳税,“这个国家一定是一个幸福安康的国家”。
但是,需要注意的是,这种做法并不是有效率的公共财政制度。理论上:一是行政垄断的国有资产因缺乏价格机制陷于低效,相当于加重税收负担;二是股权财政与现代国家制度和现代财政预算制度是相悖的。
现实中,地方政府一旦切换成股权财政,又可能像之前的国有城投平台一样,在各行各业设立一系列国有企业,采用行政垄断的方式控制市场,挤出私人投资,增加税收负担,恶化营商环境。实际上,依靠行政垄断获取的国有收入,其本质就是向国民征税,并未带来财富增量。国有企业经营“收税”、出售国有土地“收税”和正常税收“三管齐下”,宏观税负大增。
土地财政固然要破除,但股权财政同样不可取。股权财政只能作为权宜之计、应急手段和过度策略:一是地方盘活国有资产拯救地方财政(慎用);二是要求央企国企大规模上缴利润,大规模划拨国有企业股权充实社保基金(大用)。
政府债务问题还是回归到一般性逻辑去解决。
财政扩张:软性约束,硬性约束
地方债务为何失控?
需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。比如,独山县,一年财政收入10亿,欠债400亿,如果你是投资者会借钱给它吗?比如,遵义道桥,负债457亿,如果你是银行会同意展期20年吗?
有人说,这是地方GDP锦标赛和投资增长模式造成的。但是,投资增长模式一定会引发债务危机吗?有人说,这是因为财政纪律松弛,没有法律硬约束,地方债务无序扩张。像前两年清零隐性债务,城投债立即就刹车。但是,城投债立即刹车,是降低了风险还是诱发了风险?
我们可以用科尔奈的软约束理论来解释。
科尔奈是匈牙利经济学家,曾直接参与了匈牙利国家转型中的经济改革,影响了吴敬琏等一大批中国经济学家。最初,科尔奈试图用“软预算约束”的概念来解释计划经济下的短缺现象。他发现,政府长期救助亏损的国有企业,导致国有企业对成本和收益不敏感,预算约束失灵,经济效率下降,进而引发短缺。
晚年,科尔奈愈加意识到“软预算约束”实际上是缺乏价格约束。后来,经济学家结合弗里德曼的价格理论,将“软预算约束”上升到价格的一般性去分析。
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,在一个不完全开放经济体中,制度(法律)约束属于软约束,只有价格约束才是硬约束。
自由价格,可以调节供给与需求,同时也在配置收益与风险。在自由市场中,家庭和私人企业根据价格(利率)来配置控制债务规模,同时独自承担相应的风险。一个家庭成功地按揭贷款买房,享受了借债投资(消费)带来的好处。一家私人企业过度借债扩张业务,结果债务“暴雷”,其股东承担着企业破产清算的风险。同时,银行和债权人也会根据债务人的信用和利率放贷。
为什么地方政府过度举债?
原因是政府债务市场不是一个充分自由竞争的市场,价格机制失灵,无法有效地调节供给和需求、配置风险和收益,难以奖励或惩罚借贷行为。城投平台是国有的、商业银行是国有的、城市土地也是国有的,地方政府依托城投平台向国有商业银行贷款购买和开发土地,实际上是以类似计划的方式盘活土地资产,进而将其转变为财政收入。
在这个过程中,一系列计划行为不受价格的奖励和惩罚,没有人为此付出直接的相应的代价。城投平台向国有商业银行借钱,对利率不敏感,负债累累依然大肆借钱;国有商业银行的利率本身不是市场化,贷款行为受价格约束弱,而且存在体制倾向和权力干扰,城投平台奄奄一息依然“输血”;政府作为土地的唯一供应方,通过银行贷款和控制供给来推动土地价格上涨,国有土地价格也容易失灵。
由于利率价格失去了信号、供给和风险调节功能,直到城投平台债务“暴雷”,才知信贷扩张过度、信贷供给过剩、债务风险失控。而如今,地方债稍微还有一点价格刚性约束的就是由债券市场定价的城投债。
为什么制度约束属于软约束?因为制度约束改变了公共用品的价格失灵和公地悲剧的问题。美国可能是一个制度密集度最高的国家,但是国会给联邦政府设置的债务上限还是一次又一次地被突破。当然,这并不是说制度约束不重要,相反,我们还需要大量的制度建设。
问题是,如何才能对财政和债务实施真正有效的硬约束?
国家市场化——只有引入价格机制才能形成硬约束。
我在《国家市场理论》中第一次提出国家市场理论的概念。这是一个公共选择理论的议题。国家演变的历史其实是一个国家市场化的过程。按照奥尔森的国家理论,从“流寇”到“坐寇”,意味着国家的诞生,同时也意味着国家市场化的起源。从“坐寇”国家到全球化开放经济体,国家的公共用品持续走向全球市场化。
正如瑞典学派维克塞尔和林达尔的公共理论所提出的那样,由于公共用品的不可分割性,人们无法通过减少或增加需求来调节边际效用,只能求诸于税收价格。换言之,国民通过纳税来“购买”一整个公共用品套餐,包括公共教育、医疗、司法等。
回到地方债务的问题上,我们需要建立一套基于市场契约的现代财政收支体系。民众向政府纳税,购买政府提供的公共用品。税收就是民众购买公共用品的所有经济成本,政府不再通过各种费用、垄断性的国有企业来征收额外的税收;同时,政府基于税收发行债务。这是国家市场化的关键。
不过,由于全球人口流通受限,税收价格通常也不是自由价格,公共政策对不同的人产生的的边际效用不同的。这导致公共用品的价格失灵,容易引发公地悲剧:一是对税率多少的争论,人人试图干预公共用品定价,尽量压低成本;二是对公共用品分配权的争夺,人人试图占用更多公共品,尽量提高个人边际收益。
除了推动人口流动外,我们还可以在公共用品中引入更多价格机制对财政、税收和债务进行约束。
一是利率市场化。解除商业银行的行政垄断,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,政府向债券市场借债,债券价格对政府借债行为构成硬约束。只要国有商业银行持续给地方政府输血,地方债务定然是无解之题。
二是货币国际化。全球央行超发货币导致利率长期低于中性水平,为政府低成本债务融资提供便利。利率约束机制被破坏是包括美国、日本在内的全球主要国家债务失控的重要原因。尽管美元、欧元和日元已相当国际化,汇率下跌对货币超发也构成一定的约束,但是央行的垄断地位依然不可撼动。中国需要通过资本跨境流通来推动汇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,以汇率价格来约束铸币权,调节信贷闸门。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责任编辑: